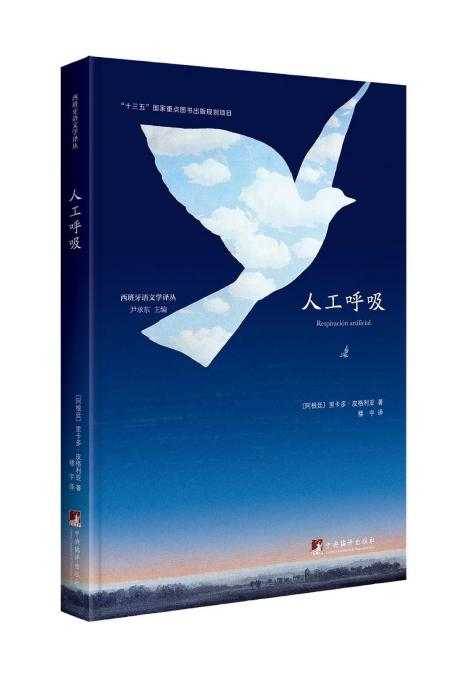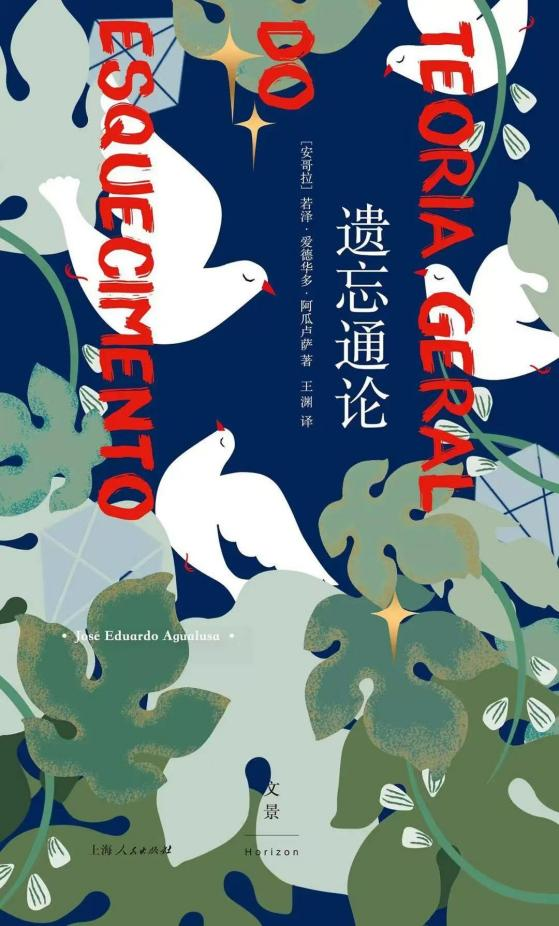
推荐理由
读过阿瓜卢萨作品的人常常会说,他是个“讲故事的天才”,这点在《遗忘通论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这本小说没有采用宏大的叙事框架,而是选择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切入点:一位名叫卢多维卡的女性,因恐惧安哥拉内战的暴力,将自己封闭在罗安达的一间公寓里长达三十年。
卢多的自我隔离成了一个特殊的观察点,让我们得以窥见战争中的安哥拉社会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她的日常生活:她如何收集雨水、如何用家具和书籍取暖、如何用姐夫藏下的钻石作为诱饵捕捉鸽子充饥。在这个过程中,个性鲜明的角色一一登场,所有遗落的线索、不经意中的细节,都环环相扣;他巧妙地构建出一个文本迷宫,让读者在虚实之间穿梭,一步步陷入他所营造的叙事游戏,直到关于“记忆”的真相水落石出。
卢多是一个因恐惧而自我封闭的人,但她也在废墟中坚持着诗意和尊严。她写石榴的光芒,写无花果树的“叛逆目光”,和一只叫“切格瓦拉”的猴子搏斗,在混乱中固执地守护生活的秩序。对她而言,遗忘不只意味着耻辱与恐惧,也是一种鲜明的自我宣言。她主动背对世界,从窗口观察一切,这本身已是一种态度。而后来走进她生命的人们,则慢慢将她从极端拉回现实,重新找回平衡。
安哥拉在小说中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,更是一个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心理空间。消失的部落“新希望”,专门收集失踪故事的记者,吞下钻石和诗歌飞走的鸽子……当有人想要忘记时,有人却在拼尽全力记得;当记忆过于沉重时,为了继续生活下去,人们又转向遗忘的温柔乡;而所有人都快要忘记时,过去丢下的线索、当下沉默的物品,仍固执地做着一切的见证者。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如何在暴力中被撕裂,又如何通过个体的记忆和叙述重新连接的图景。
阿瓜卢萨笔下的人物既相互救赎又相互伤害,没有皆大欢喜、过分浪漫的结局,而是在忏悔、沉默与有限的宽恕中艰难前行。雇佣兵热雷米亚斯·“刽子手”在坦承自己的罪行后获得解脱,却从卢多手上实现了最后的请求,而此时的他已被人遗忘,却仅仅攥着一段久远的记忆;秘密警察蒙特一生都在用恐怖的手段追杀拷打革命者,在生命的终点却为了心爱之人被电视天线砸死,遗忘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;而卢多最终推开房门的那一刻,既是她个人历程的终点,也是新生活的起点,她决定接纳她的记忆。历史从不会真正结束,遗忘不会真正发生,记忆会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。
《遗忘通论》中的人物并非孤立存在于这一本书中。熟悉阿瓜卢萨作品的读者会发现,许多角色在他不同的小说间穿行。《贩卖过去的人》中那只被称为黑夜小上帝的壁虎,在本书中重新出现;《雨季》中的女诗人莉迪亚虽未直接点名,却在监狱场景中悄然现身;而那位残暴的秘密警察蒙特则是跨越多部作品的老熟人。这种互文性使得阿瓜卢萨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更大虚构宇宙的一部分,这些角色在不同的故事里迁徙、生长,而读者每读一本新书,就像在拼图中又找到了一块缺失的碎片。
值得一提的是,阿瓜卢萨成功地突破了人们对非洲文学的刻板印象。他打破了非洲文学常被套用的“苦难叙事”预期,以独特的方式处理历史创伤。他的文字融合了葡语文学的优雅与非洲口述传统的活力,既有对殖民历史的反思,又不乏幽默和讽刺。在讲述国家创伤的同时,他提出了关于人性的普遍问题: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记忆共处?遗忘是否真的是一种背叛?而文学,或许正是那只反复在文中闪现的壁虎;它在人们选择睁开眼睛时,安静地趴伏在牢房的白墙上,“既是旁观者,亦是上帝。”
在《遗忘通论》的世界里,没有一个故事是孤立的,没有一段创伤能被彻底封存,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孤岛。正是这种深刻的相互联结,使得这部小说超越了特定的历史背景,成为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。